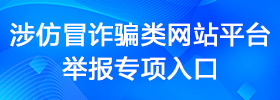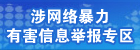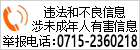走进祝家楼、石屋洞
这些年,我把业余生活的重心多放在游历山水和读案头的书上。读山读书,读得痴迷,读得辛苦,也读出了敬畏,有灵光乍现的欣怡慰藉自己,储满平庸和轻狂的心得以沉静。
我太爱幕阜山脉这方水土,每每听说有好所在,便一脚油门,一部手机,叫上知己二三人说走就走。山一程,水一程,无论多远,枯燥与乏味是没有的。清·黄遵宪说“地长不能缩,翼短不能飞”,恨天高水长不能插翅而飞的心境,也不会有的。去年和一帮文友去祝家楼游石屋洞,印象深刻,但迟迟没写文字,倒是留存的一组照片,让我情不自禁,拿来常与外人道。
辛丑年腊月某日清晨,在文友吴世湖的引领下,一行人从通羊城出发,过板茶大桥,车才进祝家楼方向的山岔,路陡然由平地崛起,山雾浓重,锁清寒,也锁视线,十步之外便不知出没。山逶迤如墙。一段三公里的山路,走得艰难,却也有几分刺激。
祝家楼是大畈镇一个行政村,群山到这里突然收住脚跟,向东一折,往西一甩,竟空出一片大洼地来。最空旷处要数收割后的稻田,中间一条石板路,很有沧桑感。石板有一块无一块的,如池塘残荷排列,传说最早是清末道光年间儒学生进山求学的必经之路,将近两百年了。环视四周,不远处一字藏塔,约半人高,用四楞起线的石块堆砌,如今唯底部一层幸存。弥散沉静古朴之气的熔纸炉支离破碎,空洞的腹腔里仿佛隐藏着时间的脸,有旧书本一样的命运和肤色,修之又难复,弃之又难舍。没有存照和文字记载,我们怎么修复都难以回到从前——时间的参与感是任何技术复制不了的。紧邻的七八棵柏树有120余年树龄,主干多两搂粗,枝柯遒劲,叶却和顺无骨,垂坠如长须,岁月便在整日飘飘忽忽的悠然中遁去。新老房屋依坡而筑,屋与屋的拐弯衔接处,要么种树,要么作菜园,有的围栏喂鸡,有的掘池养鱼,所作用途皆依屋主意愿,随地赋形了。偏安一隅的村落俨然一处世外桃源。
四围的山,山体高拔,峰入云霄。一条蜿蜒而上的路尽头是周步山,石屋洞就藏在半山腰。此时初阳淡出,云开雾散,山里的空气变得亲和起来。山路空寂人,旁边支立着数不清的茶树,间或几棵老梨树。这时节的茶花在枝头活成标本的模样,叶子却是碧青青的生机。茶树依坡而上,层层递进,漫坡漫岭的列阵,俨然兵临城下。风温柔地吹,枝头大小叶片碎金般的光点闪烁不定,晃着路面也晃人眼,友人身上的白衣仿佛有疏影横斜。梨树色黑,赤裸裸,瘦骨嶙峋的样子。车沿山路绕来绕去,无论从哪个角度,呈现给我的是一副立体水墨丹青。
得知半山腰的那条支路是为开发石屋洞而修的,且石洞在前方不远,一行人便嚷着徒步上去。山路在别处都是爬,这里却是登,身体一直往前倾。眼前一簇石林方圆数里,不断向前伸展。脚底的石块棱角锋尖,每个人都走得小心翼翼。山路下一丛丛灌木,全被藤蔓密密缠绕,全然不见树干树桠,圆润如大鼓,偶尔有一两声鸟唤。随意摇动一根枯藤,能拉动,扯不断,却惊动一窝野鸟群起而飞,鸟粪哗哗掉落。石生得很大,很野,与树与荆条相互拥挤。中有一树,两握粗,树身挺立,从一块巨石的中心冒出来,出石丈余才生横枝,显然已成材。我兴致大涨,忙去寻它的根,扎根的土,但没找到。地面不时出现一两个怪状的石头,有几人宁愿背负恶名,正在捡拾一两件惟妙的石头,准备返回时撸走。我也动了心,但没动手,因为搬不动,只好呆呆地看那缩骨蹇背不肯起身的背影,看得久了,已不识哪是石,哪是人。
恍惚间,已到石屋洞口,口径宽约三车道,呈虹形月样的飞拱,地面潮湿,滋养了一两丛小草,与脚踝齐平,寡寡的不成片。洞顶卵石倒悬,个头都不大,乍一看像极了夏天出齐星星的夜空。越往洞里走,越见水滴石穿的景象。石洞结构错综复杂,境界渐进渐变,像人像物的石头让人挪不开步伐。洞顶有数处,水滴落不停。一块十多米宽的岩石,厚不可测,形状也不规则,前低后高,石头自然堆叠,青苔抱石而生,顺势而曲。低处是一连串上下错列的浅洼。小洼小如砚池,大洼大若浴盒,都聚有水,但深不及半指,便疑心是云南元阳灌水期梯田的浓缩版。水平如镜,静而不流,倒映洞顶,也倒映人影。我才一凑近,就看到自己满头的脸,满脸的头,像个怪物。忙移开身子,又怕滑倒,轻踏碎步仍要紧盯着石面,又发现,看似平整的石面竟生出一楞一楞的线条,如褶皱的沙床,潮汐的曲线,大理石的斑纹,或是某种动物皮毛上的肌理,还有的线条似曾相识,却说不出到底像什么。更大的窟窿或石坑没有积水,也没有规律地分布。一窟大如房间,有门有窗,地面平整;一窟开口处斜倚一块偌大的仄石,缝隙仅容成人侧身进出,像盖板才被揭开,又有随时要盖上的危险。不敢喊,更不敢进,丢石头进去,好一阵才听到两石撞击的声音。又见一木桩上接顶下着地,是人为加上去的。这才知道,洞没有底,也没有顶,便怀疑整座山都是空的。果然,向导说洞长约十公里,与西侧石航山那口洞是相通联的。猜想,动荡年代这洞必作藏身遁世之用了。事后在洞前石屋里看到资料,果然,这洞就有与战乱相关的故事,也有佛教的传说。据说有洞庭十三重,通山地名由来也因此洞而起。
石洞寒凉,不宜久留。看过了饭点,有人终忍受不住饥饿,大声催促,一行人这才陆续出洞,几乎都是一步三回头地走出来,头发湿贴着脑袋,如雨中鸡。
石屋洞与隐水洞遥遥相望,距离不过数里。同样是溶洞,一个遗世之美早大白于天下,一个羞答答,仍如女子待字闺中。都是洞,运势却迥异。有些美甘于寂寞中,是要把自己淀到极致,无意轻率地受世风之扰。
当地人像养了个好闺女,总想把它嫁出去。此洞目前正在招商中。地坪不够用,先掘者还是建了石屋,这屋就半依了山,半凌空而出,一为开山工住宿之用,二为来此访孤问独者提供便利。在木板和玻璃罩严的石屋里临窗远眺,窗外风云往来,枝叶霍霍作响,可想夏日必是清凉的,舒适的了。谁也想象不到,昏暗的厨房里,从火炉上方的石壁伸出两株青藤,藤条细如线绳,叶片活泼泼的鲜亮如新。人顿时恍惚起来,一时不知是梦是幻,以为春满人间,在品享春的杰作呢。
树密岩高的洞口背光,文友仍提议要在门前拍照留念,欣欣然,几张笑脸就与石屋洞定格了,祝家楼及石屋洞从此深入我心。恰《通山周刊》主编约稿,我重读照片,庄严对待,记下这段文字。
但愿祝家楼与石屋洞能有观者不绝的那一天。












 鄂公网安备 42122402000111号
鄂公网安备 42122402000111号